營口之窗網(我要分享“營口故事”)《知青往事 》
作者:張世代
一,幾個滿意
記得是德玉(同一青年點的知青)的兒子結婚那天,我們夫婦剛剛邁進王家的門,坐在炕上正喝著喜酒的二濤高興地對我說:“大哥,那年在供銷社,你請我和小社吃餅干、喝汽水,管夠,真夠意思!” 二濤的一席話,讓我憶起了我下鄉時的一段往事。
那年秋天的一個上午,隊長有些頭痛地對我說:咱們隊里南邊的那片條子(編筐用的條槐)地,讓人偷了不少。世代,你去管一管。 領了這道命令,我也頭痛。那片條子地與南隊地挨地,南隊的一些人常到這片條子地里偷割條子。要是偷偷地割一點自家用倒也可以不管,可問題是,這些人的膽子越來越大,竟然在大白天來割條子。隊里派了幾次人過去,剛一露頭,偷割條子的人就如同驚弓之鳥,頃刻間就跑的無影無蹤。
我帶了兩個小兄弟——二濤和小社來到村里的供銷社,要了幾瓶汽水、二斤餅干,以柜臺為桌子,我們就一起吃喝起來,邊吃喝邊謀劃這次“逮人”的行動方案。
依據小哥倆的建議,吃過晌午飯,我們三個人就從三隊向西南方向潛行。這次行動很成功,我們從后面堵住了正在埋頭偷割條子的人的“逃跑”路線,一下子就逮住了5個。“押”著“俘虜”,我們凱旋回到了隊里,把“俘虜們”交給了生產隊處理。 事后隊長對我們的“成就”大加贊揚。
就這樣,幾瓶汽水、二斤餅干換來了: 領導滿意; 社員滿意; 小哥倆滿意; 我更滿意。
二, 仍在行走的車
無數形形色色的,有著不同聲音的車輛,每天從我們身邊駛過。 在遠方的他鄉,一輛業已很舊了的木制獨輪推車,仍在緩慢地轉動著它那已磨損了的輪子,默默地為它的主人繼續奉獻著自己。
在那個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年代。 山鄉里一個質樸青年,非常希冀能有一輛使他的朋友雙肩不再被扁擔壓的紅腫的獨輪推車。他覺得應該為他的朋友實現夢想,以此用了不知多少個清晨、黃昏和幾個白天,揮斧子拉木鋸,為我這個身為勞動組長的朋友做著私車。 一輛當時式樣的獨輪車出現在這個小山村時,引來了無數鄉親們的羨慕的目光。 滾動著的車輛,吱吱地壓著黃土地的時候,我的這位朋友的面容是不可名狀的幸福。
車開始了它的行程,人與車共同磨礪在風風雨雨中,人走得白霜染鬢,車走得蒼老呻吟。春華秋實的勞作,被重荷折斷了一條臂膀的它,帶著愈合后的傷口,仍以堅韌的腳步,踏過泥濘和碎石繼續丈量著田野的方圓。 剝去血肉,人的錚錚鐵骨如同車軸一樣不可彎曲,負荷著生活的沉重。 車與人共同留下曲折的車轍,人與車血脈相通,筋骨相連。
二十七年后,我又與這輛車相逢,感嘆時光匆匆與友誼彌固的淚,在酸楚與喜悅中迸發,車又逢故,回首著滄桑往事和榮辱不驚的歷程。 車亦知道路再遙遠,也終有盡頭,所以心中總是閃爍著不滅的希望,正如人也深知生命的旅途中,雖然會有坎坷,但更有不折的友誼。
三,不能忘卻的往事
轉眼之間,我已到了知天命之年,很多往事就像看過的電影和讀過的小說,已經非常模糊了。然而,有一件小事,我卻始終沒有忘記,我覺得它可能伴隨我終生。
1968年9月,我下鄉來到復縣三臺鄉桂林村。第二年端午節前的一天,晚上輪到我的班,是遛一頭生了病的牛。 來到還很陌生的村子南頭時,天快黑得看不清人了。不遠處有幾個人,聽聲音都是女性。 “是青年點的小張”。看來她們的眼力真挺好。但她們很快散去了。真奇怪!總不至于是因為我和一頭牛的到來,把她們嚇跑了吧!我當時直想笑:農村的新鮮事還真不少。 沒走多遠,她們又追了上來。我還在愣著摸不著頭腦的時候,兩個衣兜里已裝滿了熟雞蛋和那種當地山上長的叫什么“薄葉”包的粽子。她們沒有留下一句話,又都走了,夜色很快就淹沒了她們的身影。我恨我自己當時怎么就沒對她們講出一句感謝的話來。
吃著還帶著溫熱的粽子和雞蛋,仔細的搜索著記憶中的每一處角落。沒有,自己真的沒有為任何一位鄉親做出哪怕是一點點的貢獻來。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該稱呼她們大娘、大嬸、姑姑還是嫂子,但我永遠不會忘記這片曾給了我許多溫暖的土地和那些善良的人們。
四,最后的時光
隆冬的一個日子,在哀樂低徊的悼念大廳里,我含淚注視著屏幕上強子的遺像。 國慶節后的一天,我去老同學強子家看他,離開時,他一直送我到樓下,他怪我為什么不騎電動車來,否則的話,他會與我一起去體驗新建成的遼河特大橋。 我約他:來年春暖花開后,我們再一起去看大橋。 此時的強子步履仍是那樣的矯健有力,說話的聲音也仍是那樣的洪亮,看不出來他是一個有著重病的人。
十一月的下旬,我搭便車又探訪了我們曾下鄉插隊的地方。在村子里,在那落戶的同學和鄉親們,仍向以前我來時那樣與我高興而又親切地攀談,他們又如以前一樣又提起了強子,他們關切地問候他從這兒參軍走后的一切,臨走時鄉親們又如以往地托付我代他們問候他和他的家人。 在插隊做知青的那段日子里,由于強子的努力拼搏,他在鄉親們心中形象很是光輝。
從鄉下回來的第三天,我興沖沖地來到強子家,也同以往一樣,當 年下鄉的地方只要有了什么訊息,我都會忙忙去通報給強子和與我共同患難過的同學。 我按響了強子家的門鈴,過了好一會,門才開了不大的縫,強 子的妻子蓮看清了是我,又稍稍地遲疑了一下,才將門縫繼續放大。
我進屋后隨手帶好了門,當我回過頭時,我猛然呆若木雞地立在那里。
強子正神情呆滯地坐在雙輪醫護車里,對我的到來及屋子里的一切竟然熟視無睹,目光無定地游弋著。 蓮低沉地告訴我:那次我走后,強子的病情開始惡化,特別是近十天以來,大小便開始失禁,記憶也大部分喪失了。 看著塑料袋里的剛剛收拾完的穢物,我好像明白了一切——強子已進入了一生中的最后時光。
我心緒不寧地幫著蓮整理好強子的衣服,又將強子摁坐在輪椅上。由于強子的身子重,坐著有些搖晃,我扶住他,蓮用寬護帶攔住了強子的前身。強子的腿又不自覺地踢動起來,我便半跪著用手按著他的腿,等到他的腿神經順應了不動的時候再放手。 看著周身著裝利落的強子,我知道這是蓮付出的太多了……。
蓮是一個偏急、又不是一個十分喜歡做家務的女人。 強子耷拉下來的右手,隨便地碰到了我扶在車把上的左手,只這一小小的碰撞,卻突然撞開了我已漸漸遠去的回憶……。
強子和我一起下鄉,在同一鋪炕上,睡在我的右側。那次也是一個隆冬的日子,在生產隊飼養員的屋子里,早已蓄有矛盾的我和他,不經意地不知道誰先碰撞了誰的手,導火索立即點燃了炸藥,他和我由爭吵升級到了亮開拳腳,幸虧被鄉親們阻止,“戰爭”才得以沉寂下來……。 他參軍走后,我也抽調回城。
強子復員回到家的第二天,就匆匆地跑來看我。他說這幾年想同學可把他想壞了,尤其是我。 以后同學相聚時,我們常常談起上學、下鄉勞動以及互斗,還有現在,還有那個已學會叫他外公的外孫。 我的眼眶里已浸滿的淚水。
這時仍半跪著扶著車的我,看到蓮正用雙手撫著強子的雙頰,輕輕地聲音里帶著悲愴與慈愛,像是在對一個孩子述說著:強子,你怎么了?你能醒過來聽我說話和我一起炒菜嗎? 聽到一個女人知盡人間的話,我的心中地心之火,當即沖騰起來。 若不是顧慮到會嚇著熟睡的外孫, 若不是顧慮到會加深蓮的悲愴, 若不是顧慮到樓下的人會跑上來抗議,我一定會揮手跺腳無視天下一切地嚎啕大哭起來!
男與女在一起成為一對夫妻后,相互間會有指責和爭吵,也會有揮動手臂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更會有舉著戶口本鬧著去離婚的時候…… 可一旦他或她在病重的時候,他或她用雙手撫著他或她的臉頰, 慈愛地說:你醒醒,醒過來,再回到我們從前日子里的那一刻,什么以前的爭吵、什么不愉快的一幕幕當即都會化為烏有!
只這輕輕地雙掌一撫,作為一世夫妻的情誼就足夠了。 永遠不會成為圣人的對對夫妻們,生活中不會總是山花爛漫,也不要總是去要求對方如何如何…… 夫妻之間,只要有一生中最后時光的相扶就足夠了!
附:攜女兒重游舊地
文/張世代
仍是那條蜿蜒的山道
留有父親當年的足跡
上山下鄉六年
曾有彩虹冉現
但終被風雨吹散
二十年后重踏舊地
父女心緒各異
女兒稚望山川細河
父將一切故事攝入花里
(1994年8月20日于原下鄉地-一復縣三臺鄉桂林村)
作者簡介:
張世代,男,1951年生。1968年9月25日從營口市第八中學下鄉到原復縣三臺公社桂林大隊第四生產隊務農,期間多數時間做木工工作。1974年末抽調回城,在二建公司做瓦工。1976年末到漁市房產管修所做木工到退休,期間曾做個體中醫生工作。
主審評語:
張世代老師是中醫世家,祖父和父親都是中醫傳人,并有醫學著作出版。1968年他和他的八中同學一起奔赴復縣下鄉插隊,開始了長達六年的知青生涯。艱苦的生活條件,坎坷的人生經歷,并沒有磨滅人間的友誼和真情,那還帶著溫熱的粽子和雞蛋,每每都在夢中縈繞,時刻溫暖自己的心窩。正是這些真摯的人間善愛在心中,閃爍著不滅的希望,并始終圍繞堅守至今,雖然五十年過去至今延續不變。
即使回城以后,當年的知青之情也延續不斷。這是真正的戰友之情,鐵哥們之情。讀來使之動情,感慨萬千……。
文章敘述清晰,層次分明,有文學功底。
——主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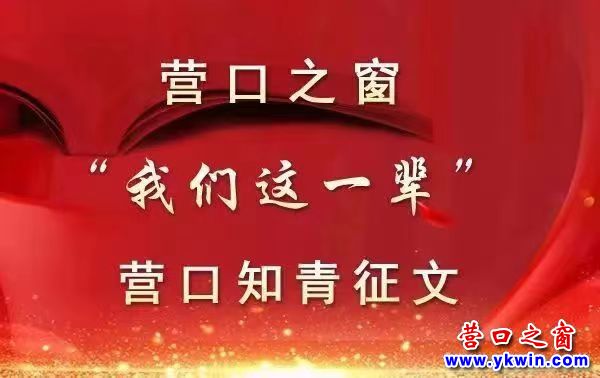
供稿作者:張世代(知青,68屆 復縣)
本期主審:趙洪柱(知青,特約主持人)
原創發布:營口之窗官網
更多信息,請關注營口之窗公眾號:營網天下
版權聲明:營口之窗所有內容,轉載須注明來源,禁止截取改編使用。

上一篇:記憶猶新的瞬間——營口之窗網知青征文
下一篇:二壯的婚事——李同雁